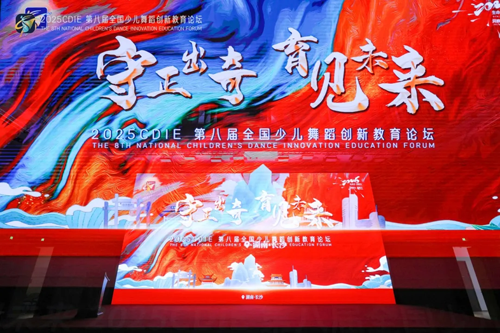作者:袁田田 袁坤 来源:新华网“学术中国”— 学术理论文献
社会性质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总和,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党推进理论创新的现实依据。第一个历史决议以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为切入点,围绕革命道路展开具体思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筑牢理论基石。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阐释
处理革命问题的前提依据,在于辨明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个历史决议作为党重大理论成就的标志性结晶,不仅在关键时刻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党史经验,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框架下全面而透彻地解读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一)社会性质的判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
社会性质是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反映了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关键属性。第一个历史决议敏锐地察觉到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强调其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1]的基本国情。在半殖民地性质方面,自 1840 年以来,帝国主义势力借由军事侵略威胁中国签订多个特权条约。割占领土、设立租界,使中国丧失了独立政治主权;巨额赔款、掠夺航运与矿权,操纵中国经济命脉,加剧民生困顿;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加速文化渗透。不仅从诸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国,更将中国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半封建性质方面,农民不仅要生产自需的农产品,还要缴纳地租,朝廷又强制其承担繁重徭役,以维持上下官吏的俸禄和军兵的粮饷、维系国家运转。可以说,封建与剥削紧密相连。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从秦到清的中国帝制,可封建剥削并未彻底清除,仍旧在维系。地主豪绅通过高额地租压榨农民、军阀混战导致民生凋敝、封建礼教禁锢民众思想。极少数买办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掌握绝大部分资源,而广大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被压迫在生存边缘。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分析帝国主义入侵与本土封建势力的勾结,从实质上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两大特征——政治上的半主权状态、经济上的封建残余与资本主义渗透并存。
(二)主要矛盾的剖析:“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于剖析敌友。第一个历史决议研判近代中国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共生关系,进而深挖社会矛盾冲突的总根源,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2]
。决议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放在首位,同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及其残暴统治,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但“左”倾路线者却忽视了民族危机加剧的局面,拒绝了中间阶级积极的抗日政治倾向与救亡运动,不加以具体分辨,而偏激地采取“打倒一切”的策略。通过阐述列强侵华是民族独立的最大障碍,强调近代中国的首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侵略下主权沦丧的民族矛盾。同时,决议还突出了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强调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为革命爆发积蓄了巨大能量,但“左”倾路线者低估了农民的需求与乡村根据地的重要价值,造成革命受挫。通过阐述封建剥削导致农民极端贫困,强调近代中国的另一主要矛盾是半封建腐朽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借由批判“忽视民族矛盾”和“低估农民问题”的两种错误倾向,第一个历史决议昭示了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盘剥下的极端生存危机。
(三)历史任务的明确:“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在准确把握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矛盾的前提下,第一个历史决议剖析阶段性斗争的时代命题,明确中国革命属于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3]
。帝国主义的压迫使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中国的首要重任,封建制度的顽固则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这一表述不仅呼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内在本质,更揭示了中国革命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典型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中国革命兼具对抗外部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内部封建秩序的社会民主革命的双重性质。这一历史任务的设定,正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所反映的核心矛盾的直接回应。
二、准确的社会性质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
第一个历史决议准确阐释中国社会性质,明确革命历史任务。以“两半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为基础,从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生命力。
(一)理论创新:“两半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半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直接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行动指南,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革命时期的代表性成果,其理论起点正是近代中国的“两半论”。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构来看,“两半”的社会性质昭示着中国的主要矛盾和革命对象,进而决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使命。为此,革命过程中必须明确“动力从哪里来”这一理论难题。最终,在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团结广大民众,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所以就思想逻辑关系而言,有这样一个理论发展过程:“两半论”判断——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可以说,“两半论”为后两者在理论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坚实支撑。
“两半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经典分析与全新论述,庄重地写进了第一个历史决议。“两半论”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深度融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双重属性的判断。这一分析范式,打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单线序列发展观,突出了世界时局的变动,也突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差异性,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标志性成果。
(二)实践指导:“两半”社会下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策略
“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一个历史决议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与复杂的社会阶级结构,强调“两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武器,团结形成同盟阵线。一方面,决议从理论上分析了近代中国“两半”社会性质中的阶级构成,进而探究了革命的主体力量与依靠力量,强调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核心;而深受压榨的广大农民是革命的主体;至于在困顿时局中难以自存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样是革命动力。三者的联合使革命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决议从实践上肯定了党争取同盟的革命行动。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提出的“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4]策略,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长征与抗战期间取得了辉煌成就。革命斗争胜利的实践证明,革命必须由受压迫的社会底层发动,建立统一战线以集中力量对抗共同的敌人。
“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第一个历史决议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出发,就近代中国城市与农村不同区域的敌我力量,里程碑式地总结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道路。相较于反动势力在城市高度集中的军事与政治控制,农村的统治则相对薄弱,更有利于开展土地革命、组织群众武装、培养革命骨干。这一社会性质的矛盾与社会结构的空间差异,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照搬俄国“城市中心论”,而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一方面,决议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指出其根源在于误判社会性质,忽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继而导致先发动中心城市的幻想与盲目。另一方面,决议事实上肯定了毛泽东在正确把握社会性质基础上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从策略上指明“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5]
,进一步凸显了农村根据地的重要作用。概而言之,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不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战术选择,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密码,更彰显了党在复杂环境中实事求是、灵活应变的能力。
(作者单位:江西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实践与经验研究(1949—1978)”(项目编号:24CDJ036);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以‘进阶性说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头脑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4DJQN021)]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23.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2.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24.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32.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27.